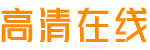中國恐龍:從科研探索到科學(xué)教育”國際研討會現(xiàn)場。主辦方供圖
10月28日,“中國恐龍:從科研探索到科學(xué)教育”國際研討會在上海舉行。全國政協(xié)常委、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周忠和以及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、中國科學(xué)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徐星接受了澎湃新聞(www.thepaper.cn)記者采訪,談及恐龍研究的現(xiàn)況和未來。
被問及恐龍是否可能從“復(fù)原”走向“復(fù)活”時,徐星院士表示,通過現(xiàn)代生物學(xué)技術(shù),未來有可能“制造”出活著的恐龍。它可能跟遠古的恐龍有一些差別,但是外形上、行為上也許是很近似的。
就恐龍物種發(fā)現(xiàn)而言,中國已是世界第一
徐星表示,中國的恐龍研究已經(jīng)經(jīng)歷了百余年的歷史,從第一代學(xué)者楊鐘健院士到2024年剛剛過世的董枝明先生,再到更年輕的一代,通過幾代科學(xué)家的積累,中國恐龍學(xué)的研究在世界上已經(jīng)樹立了崇高的地位,中國已經(jīng)成為世界恐龍研究的中心之一。

徐星院士在研討會上。主辦方供圖
“如果從物種發(fā)現(xiàn)的角度來看,中國已經(jīng)成為了世界第一。不僅如此,中國恐龍化石的許多研究,比如說關(guān)于鳥類起源的研究,已經(jīng)成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貢獻者。”徐星告訴記者。值得一提的是,兩天前,2025未來科學(xué)大獎在香港頒發(fā)。季強、徐星、周忠和因發(fā)現(xiàn)了鳥類起源于恐龍的化石證據(jù)而獲得“生命科學(xué)獎”。
未來科學(xué)大獎從名字上看是關(guān)于未來,而古生物學(xué)是研究過去歷史的。徐星表示,對于過去的認知對于人們理解生物多樣性和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演化有非常重要的意義,能幫助應(yīng)對未來的生態(tài)危機,比如在生物多樣性的銳減等問題上給予一些幫助。周忠和也講到,研究歷史的科學(xué)和現(xiàn)代總是密切相關(guān)。無論是過去、今天還是未來,生命演化的規(guī)律是一致的。科學(xué)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,或許更需要人們從過去尋找智慧,面對當(dāng)下和未來。
恐龍研究的未來:AI和學(xué)科交叉
恐龍研究如今已經(jīng)到了一個新的發(fā)展階段——融合的階段,大數(shù)據(jù)等多種技術(shù)互相融合。談及未來的恐龍研究,徐星認為更多的是要整合各種各樣的恐龍化石數(shù)據(jù),而這些數(shù)據(jù)來自各種新的成像技術(shù)、化學(xué)方法,甚至人工智能,從而分析恐龍演化的規(guī)律,研究中生代地球的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。
如今,已經(jīng)有一些年輕學(xué)者開始使用人工智能技術(shù)進行恐龍研究,但尚處于起步階段,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,未來AI在恐龍研究當(dāng)中還將有很大的提升空間。“希望新一代的學(xué)者能夠成為新研究方法的引領(lǐng)者、新技術(shù)的引領(lǐng)者,甚至是新理論的引領(lǐng)者。”徐星說。
古生物學(xué)是歷史悠久的、古老的基礎(chǔ)學(xué)科,也因此有著豐厚的、長時間的積累。發(fā)展到今天,古生物學(xué)為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呢?
周忠和認為,首先是因為不斷有新的發(fā)現(xiàn)。人類對自然的探索欲望是永恒的,這種內(nèi)在的動力和人們對科學(xué)的探索動力本身是一致的,所以這種發(fā)現(xiàn)會是無止境的。新的發(fā)現(xiàn)一定會帶來新的認識,因此人類對自然生命和地球科學(xué)的認知不斷在拓展。其次是新的技術(shù)應(yīng)用。在古生物學(xué)當(dāng)中,包括AI在內(nèi)的各種新技術(shù)不斷地產(chǎn)生影響。此外,古生物學(xué)的發(fā)展離不開不同學(xué)科的交叉融合,“科學(xué)發(fā)展太專門化了之后,就會有局限性”。
恐龍能“復(fù)活”嗎?
隨著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,從“復(fù)原”恐龍到“復(fù)活”恐龍,是否真的存在可能性?被問及這個問題時,徐星表示“未來我們有可能制造出‘活著’的恐龍”。
復(fù)原技術(shù)如今已經(jīng)取得了可觀的成果,能夠做到非常精確。早期,科學(xué)家對恐龍形狀實現(xiàn)較為準(zhǔn)確地復(fù)原,如今已經(jīng)可以對外表做到精確地復(fù)原,并且具有堅實的科學(xué)基礎(chǔ)。比如帶羽毛的恐龍化石的發(fā)現(xiàn),還有一些體表顏色多彩的恐龍,這些都有科學(xué)依據(jù),有精確的研究方法進行復(fù)原。恐龍復(fù)原確實越來越精確,這是基于科學(xué)方法的進步。
“在此基礎(chǔ)上怎么復(fù)活恐龍,是一個更有挑戰(zhàn)性的工作。”徐星解釋道,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,大家較為熟悉的通過DNA復(fù)活恐龍的路徑,應(yīng)該是走不通的。研究認為古DNA只能保存在有限的地質(zhì)時間階段,而恐龍這么古老的生物,它們的化石并沒有古DNA保存。也有學(xué)者在恐龍化石中發(fā)現(xiàn)了蛋白質(zhì)片段,但目前來看通過古蛋白獲取復(fù)活恐龍的數(shù)據(jù)也非常困難,從數(shù)據(jù)量上講,不見得是成熟可行的方案。
但徐星表示,科學(xué)研究永遠都是迎接挑戰(zhàn),有更多的學(xué)者開始采用合成生物學(xué)、基因編輯、發(fā)育生物學(xué)等領(lǐng)域的一系列新技術(shù)。他相信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能夠準(zhǔn)確、科學(xué)地復(fù)原恐龍,那么有了這些形象和認知,通過現(xiàn)代的生物學(xué)技術(shù),在未來有可能制造出來“活著”的恐龍。也許“制造”的恐龍和遠古的恐龍有一些差別,但在外形上、行為上也許是很近似的。
“100年后或者200年后,如果看到類似于霸王龍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,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會感到驚訝的。”徐星說。